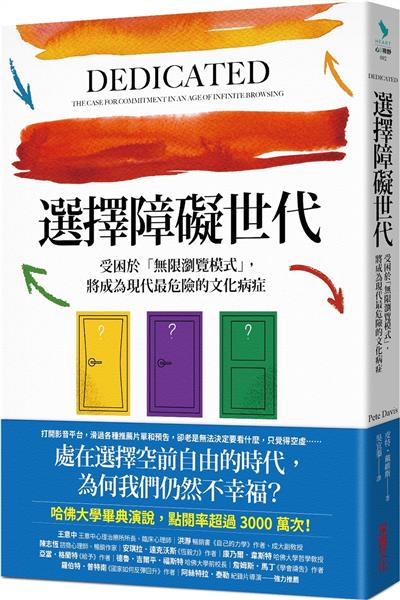- 卡達暫停生產液化天然氣 歐洲、亞洲買家將受衝擊
- 打臉中國!駐以色列代表處助2台人抵達約旦
- 快訊/對伊朗開戰後首次有美國船被打中 巴林港內美國油輪起火撤離船員
- 伊朗革命衛隊宣稱瞄準納坦雅胡總理府發射飛彈 以色列:無傷亡
- vivo「V單王」X300 Ultra 具備400mm超長焦增距鏡! 現身MWC 進軍國際
- 蔡正元有罪定讞還沒入獄!聲請再審吐苦水:被開槍險成骨灰
- 【更新】美軍3架F-15戰機遭友軍誤擊 科威特證實:飛行員成功逃生
- 伊朗頻炸鄰國 各國還不還手陷兩難、面對「不可能的選擇」
- 核三重啟進行中 台電2/13已與西屋簽約、3月底提再運轉計畫
- 質疑偵辦京華城檢察官不公 柯文哲明早赴檢評會提出個案評鑑申請
- 兒少性侵追訴權釋憲!倖存者「這簡訊」揪心 律師:痛仍希望為別人撐傘點燈
- 荷姆茲海峽封鎖影響油氣運輸 台電董座曝:5、6艘LNG船受波及
- 高通MWC首發3奈米+NPU穿戴新平台上陣! 台廠代工仁寶、鴻海和碩出列
- 伊朗宣布已555人死於美、以攻擊 黎巴嫩與波斯灣國家數百人傷亡
- AI電力需求大爆發!台電:未來5年成長1GW 是過去的2.5倍
- 中東戰火延燒!真主黨向以色列開火「成獵殺目標」傳一高層已被炸死
- 台股收跌319點 外資加碼面板雙雄!大砍這檔ETF和金融股
- 港媒爆外甥賺紅錢捐政治獻金 劉世芳親上火線曝時序打臉
- 兒少性侵追訴權釋憲!大法官狂問70分鐘律師一句話酸爆 倖存者嘆無發言權
- 信錦去年EPS 3.46元擬配3元現金股利! 低軌衛星發威今年營收占比衝2位數
「選擇障礙世代」的反主流文化者:退出「無限瀏覽模式」,長期投入某一件事物
你可能有過這樣的經驗:夜裡,你打開網飛(Netflix)開始瀏覽,想找部影片來看。你滑過不同的標題,看了幾個預告片,甚至還讀了幾篇評論,但就是無法下定決心要看哪一部電影。三十分鐘就這樣過去了,你仍然困在無限瀏覽模式中,所以你乾脆放棄,你現在已經太累,什麼都不想看了,你決定在此停損,直接睡覺。
無限瀏覽模式
我認為,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典型特徵:保持選擇的開放性。
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.包曼(Zygmunt Bauman)曾提出一個詞彙,能適切地形容我所說的這種現象──「液態現代性」。包曼解釋說,人們從不想屬於任何一種身分、地方,或社群,所以我們就像液體一樣,處於一種可以適應任何未來形式的狀態。而且不僅人們如此,人們周圍的世界也像液體一樣。我們不能期待任何工作或角色、想法或志業、團體或機構,會以相同的形式長期存在──同樣地,它們也不能這樣認定我們。這就是液態現代性:它是無限瀏覽模式,但適用於生活中的一切。
對許多人來說,離開家去外面的世界,就像進入一條長長的走廊。我們走出了自己成長的房間,來到了這個有著數百扇門的世界,可以無限地瀏覽。我看過擁有這麼多新選擇帶來的好處。我看過當一個人找到更適合真實自我的「房間」時,他們感受到的那種快樂。我發現做重大決定不再那麼痛苦,因為你隨時可以退出,隨時可以移動,隨時可以分手,走廊永遠在那裡。大多數時候,我看到了朋友們瀏覽各種房間的樂趣,經歷了歷史上任何一代人都不曾經歷過的新奇體驗。

但隨著時間推移,我察覺太多扇門帶來的負面影響。當然,沒人想被鎖在某一扇門裡面,但是,也沒人想住在走廊裡。當你對某件事失去興趣時,擁有一些選擇是好事,但我發現,我從一個選項跳到另一個選項的次數越多,我對這些選項就越不滿意。現在,我最渴望的體驗不再是新奇的衝擊,而是那些完美的週二晚上,和認識很久的朋友一起吃晚餐的時刻──那些你用心珍惜的朋友,不會因為找到更好的人而離開你的朋友。
長久投入承諾的新型英雄
隨著年齡增長,那些退出無限瀏覽模式的人反而越來越能激勵我。這些人選擇了一個新的房間,離開走廊,關上門,完全安頓下來。
電視節目先驅弗雷德.羅傑斯(Fred Rogers)錄製了八百九十五集《羅傑斯先生的鄰居》(Mister Rogers’ Neighborhood),致力於推動兒童電視節目朝更人性化的模式發展。天主教工人運動(Catholic Worker)的創始人多蘿西.戴(Dorothy Day)每晚都和那些社會邊緣人待在一起,這樣的承諾與付出對他們來說事關重大。還有小馬丁.路德.金恩(Martin Luther King Jr.),不僅曾於一九六三年時面對高壓水槍鎮壓,還於一九六七年時,主持了他的第一千次冗長規劃會議。
這類新型英雄讓我產生了欽佩之情,我開始欣賞與小時候所景仰的偶像完全不同的人物。那些「很酷的老師」在我記憶中漸漸消失了,我甚至想不起某幾位的名字;但那些慢條斯理且沉穩的老師,卻始終徘徊在我記憶中。
我高中時,學校裡有一位令人生畏的劇場人員和機器人技術組長,巴盧先生,他在學生中培養出一批不合群的維修匠和未來的工程師。他似乎獨占了學校的某個區域,裡面擺滿進行到一半的案子、數十年累積下來的技術成果,以及穿著黑色T恤的忠誠學生信徒。學校裡的大多數人,包括我在內,都有點怕他,害怕自己會妨礙到他,或者弄壞那裡的某樣東西。但這就是他那套方法的關鍵,如果你願意面對自己的恐懼並與他接觸,他會教導你幾十種工藝技術中的一種。
有一次,我和朋友為學校的娛樂表演拍了一支搞笑影片。他看了之後告訴我,我「完全不會取景構圖」,這支影片不夠好,不能展示給觀眾看。其他老師都只是為學生做了某些東西而高興,對我十幾歲時拍的影片總是給予讚賞。巴盧先生則不同,他堅持認為,如果你想從事一門技藝,就應該好好磨練。我還記得我抱怨他對我太苛刻了。
但巴盧先生的方法也有正面之處。有一次,我想在學校的庭院裡搭建一個音樂會場地。每個老師都認為這個想法很荒謬,不可能辦到。但當我告訴巴盧先生時,他一點也不吃驚。他說,如果我學會使用工程軟體,並設計出一個藍圖,他就會支持我,把這個東西做出來。這才是真正的老師──對你要求很多,但如果你致力於學習,他就會全力支持你。
我跟蓋特利太太學鋼琴,她在她那間房子的客廳裡,同一架大鋼琴旁邊的同一把椅子上,坐了四十年。當我的朋友花一到兩年的時間,自由地進出鋼琴課,學習他們想學的流行歌時──凡妮莎.卡爾頓(Vanessa Carlton)的〈千里迢迢〉(A Thousand Miles)和酷玩樂團(Coldplay)的〈時鐘〉(Clocks)是我那年代的流行歌──蓋特利太太的教學方式看起來就是老古董,她的學生不只要學習音階和演奏古典音樂,上蓋特利太太的課,就等於加入一種沉浸式的體驗,這種體驗比學鋼琴更重要,甚至比你更重要。
你不能只是每週去上課,所有學生都必須按照蓋特利太太的日程表來安排活動,像是秋季的獨奏會、耶誕節的音樂會、奏鳴曲節、六月的獨奏會──而且每項活動之前都有相應的練習,所有學生都要一起準備。你必須學習鋼琴的歷史,巴洛克時期和浪漫主義時期的區別,以及演奏結束後鞠躬的正確方式。
你也不能真的退出。中學時,有一次我問蓋特利太太,我是否可以休一年的假。
「可以吧,」她回答,「但我們這裡並沒有休假一年這種事。」
我最後在蓋特利太太那裡上了十二年的課,在那個客廳裡學到了比鋼琴更多的事情。我看著一些年紀較大的學生演奏我覺得自己不可能學會的曲子,但到了最後,我也學會了。而且因為蓋特利太太認識我的時間夠久,以她對我的洞察和權威,能提供比其他老師更深刻的建議,比如她告訴我:「你的生活步調有點快,如果你慢下來,可能會感覺好一點。」我父親過世時,多年來在各種音樂會上都會與他碰到面的蓋特利太太也來參加葬禮,這件事意義深重。從那些讓你在第一堂課就演奏〈千里迢迢〉,並在你第一次感到無聊時就同意你退出的老師那裡,你是不可能得到這些體驗的。

像蓋特利太太和巴盧先生這樣的人,以及多蘿西.戴、弗雷德.羅傑斯和小馬丁.路德.金恩這樣的偶像人物,我並不是隨便湊在一起談的。我認為他們是同一種反主流文化的一部分──承諾。他們都採取了同樣的激進行動,對特定事物做出長久投入的承諾,無論是特定的地方或社群、特定的志業或行業,還是特定的機構或個人。
主流文化的反叛者
我用「反主流文化」一詞,是因為這樣的行為,並不是當今主流文化敦促我們去做的事。主流文化敦促我們去豐富自己的履歷,而不是被某個地方束縛住;它敦促我們重視可以應用於任何地方的抽象技能,而不是只能做好一件事的技藝。主流文化告訴我們不要對任何事情投入過多情感,最好是保持距離,以防公司被出售、收購、縮編,或「提高效率」;它告訴我們,不要太認真堅持任何事情,而且當別人不這麼做的時候,也不要感到驚訝。最重要的是,它告訴我們要保持選擇的開放性。
然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,都是這種文化的反叛者,他們的生活方式與主流文化格格不入。
他們是公民──認為自己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有責任。
他們是愛國者──熱愛自己居住的地方以及這些地方的鄰居們。
他們是建設者──從長遠角度來看,他們會把想法變成現實。
他們是維護者──監督著機構和社區。
他們是匠人──為自己的手藝感到自豪。
他們是同伴──花時間與人們相處。
他們與特定的事物建立關係,並透過長期努力,來表達他們對這些關係的愛──為此關上其他的門,放棄其他選擇。
好萊塢電影在講述勇氣的故事時,通常會採用「屠龍」的形式,也就是故事中會有一個反派,而勇敢的騎士在某個重要時刻,做出了一個決定性的選擇,冒著一切風險為人民贏得勝利。所謂的勇氣,就是那個站在坦克前的人,或衝上山的軍隊,或在完美的時機做出完美演講的候選人,所展現的特質。
但我從前述長期奮鬥的英雄身上學到的是,並不是只有面臨「屠龍」式的情境才叫勇氣,那甚至不是我們應該仿效的英雄主義類型,因為大多數人在生活中並不會常常面對戲劇性的、決定性的時刻,至少不會經常碰到突然冒出來的關鍵時刻。大多數人只是面對著日常生活:一個接一個的平凡早晨,我們可以決定開始去做或繼續做某件事,或者是不去做。生活最常給予我們的,不是偉大而勇敢的時刻,而是一連串平凡而微小的時刻,我們必須從中找到自己的意義。
這些反主流文化而專心致志的英雄們,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地努力,這本身就是一件戲劇性的事了。阻礙他們前進的巨龍,是每天的無聊、分心和不確定性,這些都會對長期的承諾造成威脅。他們的重要時刻,看起來並不像是揮劍,而比較像是耕種。
※本文經采實文化授權刊登《選擇障礙世代:受困於「無限瀏覽模式」,將成為現代最危險的文化病症》部分章節,文章標題經《太報》編輯改編 。